
《漢藏兩地書》紀錄片正片
“姓名:洛桑他青,開封地區衛生學校醫師八班學生,來自西藏少數民族地區,不懂漢語。若該生外出迷路,敬請社會各界革命群眾將他送到開封地區衛生學校。”
在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人民醫院醫生洛桑他青的抽屜里,如今依然留存著一張泛黃的小紙條,那是1975年洛桑來開封學習時班主任老師為他們制作的。翻開紙條,一段塵封的記憶也隨之被喚醒。

上世紀70年代,為進一步解決西藏缺醫少藥的問題,在中央支持下,西藏提出要建立一支永遠帶不走的醫療隊,先后派出1300多名藏族青年到兄弟省市學習文化知識和臨床醫學專業技能,其中有160名藏族學生來到開封衛校(后并入河南大學)。這批藏族學生學成回到西藏后,長期扎根高原、高寒地區基層醫療衛生一線。
2020年8月,為真實紀錄這160位藏族學生在河南刻苦學習、在雪域高原無私奉獻的故事,河南鷹展文化傳播公司創始人、制片人,河南大學碩士生導師陳舉帶領團隊專程赴藏,拍攝了紀錄片《漢藏兩地書》。

陳舉導演
該片經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學習強國平臺推送后,在漢藏兩地干部群眾中引起了較大反響。該紀錄片也憑借其影響力斬獲中國高校2020-2021影視推優活動暨第十一屆學院獎紀錄片單元(教師組)二等獎、第十一屆中國紀錄片學院獎、中國電視藝術家學會“第27屆中國紀錄片學術盛典”長片好作品、中國文聯新時代小康紀實影像征集典藏活動長片類好作品、河南廣電2021年度優秀電視紀錄片一等獎、39屆河南省新聞獎二等獎等重要獎項。
今年2月6日至10日,第十一屆海峽兩岸電視藝術節海報展在福州舉行,陳舉指導的碩士班以紀錄片《漢藏兩地書》為主題的海報設計作品6幅入選。
屬于這部紀錄片的特殊記憶再次被開啟,而紀錄片背后那段不曾為人知的漢藏兩地感人故事,也在陳舉導演與正觀新聞記者長達2個多小時的對話中逐漸清晰。
緣起:偶然得知 奔赴西藏
正觀新聞記者:您當時創作這個紀錄片的背景和初衷是怎樣的?
陳舉:這個其實也很偶然,2019年9月,河大剛開學不久,我和河大校友會的老師、新聞傳播學院的老師、文學院的老師一起召開座談,其中校友會的老師講起不久前幾個西藏校友到醫學院作報告的事情,說講座進行了幾個小時,學生們聽得都很激動。當時我就多問了一句,“咱們還有西藏校友呢?”那位老師說有呀,于是便講起了那一批西藏學生來開封學習時的故事。也就是那時候,我才開始知道有這么個事,當時聽完就想著能不能做個東西,因為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所以想趁著這個契機把這個故事講好。這大概就是我當時創作的一個背景。
正觀新聞記者:當時有了這個想法后,您和團隊都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陳舉:最初我對這個故事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入,只是在與校友會老師的多次溝通中知道了喜樂、歐珠羅布、卓瑪、央金等很多藏族校友的名字,知道了他們曾在河南學習過,但對其中的一些細節其實并不是很熟悉。直到我們采訪團到了西藏,面對面接觸到了那群曾在開封學習過的藏族校友之后,他們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才被我們一點點挖掘出來。

西藏大學醫學院原院長、博士生導師歐珠羅布接受采訪
感觸:三度到訪 感動依舊
正觀新聞記者:您的拍攝大概持續了多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陳舉:我是2020年8月份帶著我的團隊,還有兩位研究生,大概15個人一起到的西藏,那一次我們在西藏待了20多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西藏的每一天都在被感動。這次拍攝算起來應該是我第三次進藏了,第一次是1998年冬春之交,當時我就職于央媒駐武警記者站,藏北高原大雪封山已超過9個月,廣大農牧民的生活生產甚至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威脅,駐藏武警部隊受命赴災區抗雪救災,于是就有了我首次進藏的經歷。第二次進藏是2014年9月,當時我在鄭州師范學院任教,受西藏米林縣教育局邀請,我和傳播學院的院長帶著學生團隊一起到林芝米林縣,為他們拍攝一部向教育部匯報義務教育工作的專題片。第三次進藏,也就是這次,是受河南大學校友總會委托,進藏尋找和采訪20世紀70年代末在河南開封地區衛校(后改為開封醫學高等專科學校,2000年并入河南大學)學習的藏族班學生。從拉薩到日喀則,從山南加查縣到措美縣,從阿里到那曲,5000多公里、20多天的高原奔波,我和團隊的小伙伴們的心靈得到了一次又一次醍醐灌頂般的洗禮。
正觀新聞記者:醍醐灌頂,這個評價還是很高的,有什么具體的故事或者細節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陳舉:感動的故事太多了。在我們的拍攝過程中,有一位校友讓我們攝制組的所有隊員都為之流淚。他就是從畢業到退休堅持在浪卡子縣張達鄉做鄉村醫生的布瓊次仁。

布瓊在羊措雍措湖
布瓊所在的張達鄉位于羊卓雍錯湖畔,當我們到達張達鄉的時候,一位身高1.7米左右、膚色黝黑、戴著一頂牛仔帽的老人急匆匆走過來,這位老人就是布瓊。
布瓊出生在浪卡子縣卡熱鄉章麥村一個牧民家庭,從小目睹了村里很多人生病得不到及時救治的痛苦,他就立志當一名醫生,希望將來能為鄉親們減輕痛苦。1975年,布瓊和其他同學一起,輾轉拉薩、格爾木,來到開封。1979年,完成學業的布瓊回到了山南地區,被安排到浪卡子縣的張達鄉當衛生員,這里距離他家所在的卡熱鄉差不多有150公里的路程。
接受我們采訪時,布瓊說,剛到張達鄉衛生院時,條件異常艱苦,只有他一個鄉醫,另外兩個村醫,整個醫院只有兩間房子,連一張病床都沒有。當時醫生出診基本上只能靠馬、靠兩條腿來解決。布瓊回憶,一次有個小孩,患了急性闌尾炎,這個病現在司空見慣,但在當時,因為沒有經驗,再加上醫療水平有限,所以顯得很棘手。布瓊介紹,那個孩子是父母騎了一個多小時的自行車載過來的,他見到那個孩子時,那個孩子臉色蒼白,疼得在地上打滾,可由于布瓊不懂外科,無法為那個孩子做手術,只能拿點止疼片,最后眼睜睜地看著那個孩子在他眼前離世。
布瓊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邊講邊哭。他的這個情緒也感染了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大家聽著布瓊的講述,都在不由自主地流淚。說起來,我也不是第一次進藏,也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故事,但聽著眼前的花甲老人這么平靜地講著他的過往,我的眼睛頃刻間有些濕潤,我們的攝影師、燈光師還有編導也都在默默地流著眼淚,布瓊的樸實、坦然和真誠深深打動了攝制組的所有成員。
布瓊在浪卡子縣基層一干就是幾十年,很多一起從開封回來的同學后來都擔任了醫院院長、衛生局局長、行署副專員,甚至更高的職務。他也有機會調到縣級醫院工作,或者到更好的環境去,但他一一謝絕了這些機會。后來,任自治區衛生廳副廳長的同學喜樂給他打電話,問他是否需要幫他什么,布瓊想了想,最后要求,幫鄉衛生院再申請10個床位編制。
2010年,在布瓊退休前,縣衛生局的領導來張達鄉看望他,讓他有什么要求盡管提。布瓊說自己沒什么要求,就是希望有機會讓他到地區保健醫院培訓幾天。
現在,布瓊的兒子也成為了一名村醫。問其原因,布瓊說,西藏地區的絕大部分鄉村都離中心縣城比較遠,村子里最需要的就是醫生,只有醫生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健康要求。他不僅讓自己的兒子學習醫學知識,還為當地培養了12名學生,他們已經成為周邊鄉村的村醫骨干力量。
淚目:漢藏兩地 師生牽掛
正觀新聞記者:40多年過去了,如今這批藏族校友們和當年的老師還有聯系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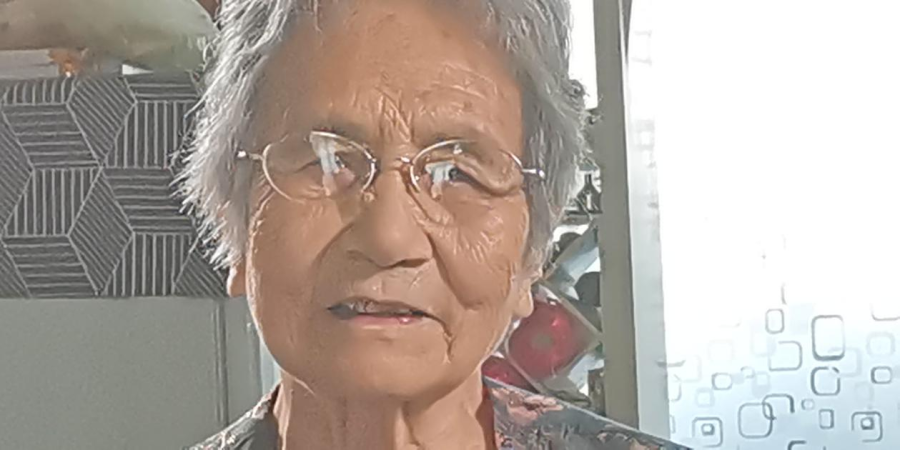
范秀云老師
陳舉:不僅有聯系,而且還十分頻繁。我們在采訪的過程中,這群如今已經退休的藏族學生回憶起他們當年的班主任范秀云老師時,幾乎人人眼里都充滿了淚水。在山南地區人民醫院洛桑他青的抽屜里,現在還保留著一張紙條,那是他們剛到學校時班主任老師給每個同學手寫的一個字條,上邊寫著“洛桑他青,開封地區衛生學校醫師八班學生,來自西藏少數民族地區,不懂漢語。若該生外出迷路,敬請社會各界革命群眾將他送到開封地區衛生學校。”洛桑他青回憶說,剛開始他們不認識漢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記得老師特別交代,一定要把字條裝好。后來大概過了一年,已經認識不少漢字的洛桑才明白了那個字條的內容。
范秀云老師現在已經80多歲了,但是當我拿著那一屆西藏班學生的照片給她看時,她可以清楚地叫出每個學生的名字,而且可以清楚地講述出他們上學時發生的故事。
在我們采訪過程中,很多同學說,他們都把范秀云老師看作自己的媽媽,有時候感覺范秀云比媽媽還親。在山南雅礱酒店,山南地區人民醫院的外科主任洛桑桑甸還眼含熱淚專門唱了一首自己寫給范秀云老師的歌,歌詞大意是:“她頭頂堆滿白雪,腰彎成了一道山梁,她擠奶走出羊圈,為了兒女們祈禱吉祥!啊,慈祥的母親,啊,媽媽,慈祥的母親!”

時任班主任(左三)范秀云老師與攝制組合影
從西藏回到開封后,我們再次去看望范秀云老師,并讓她看了洛桑桑甸為她唱歌的視頻,老人家頓時淚流滿面。
曾任西藏自治區衛生廳副廳長的喜樂說,當時上學的時候,藏族班一有問題和困難,范秀云就和其他老師一起,不惜代價,想盡一切辦法來幫助解決。所以他經常說,河南是他們的老家,在西藏最需要的時候,是母校老師培養了他們,在最困難的時候,是河南人民養育了他們。
正觀新聞記者:后來范秀云老師和這群西藏學生們有再見過面嗎?
陳舉:2009年,在這群藏區校友畢業30年后,范秀云老師第一次乘火車到了西藏拉薩。在喜樂、歐珠羅布等學生的陪同下,她到山南、日喀則等地,看望了在各個崗位上的藏族班學生。
2019年,年過八十的范秀云老師,在家人的陪同下,第二次進藏,在拉薩見到了久別重逢的學生。師生們一見面就特別感動,這些已經進入古稀、花甲之年的老人抱著范秀云失聲痛哭,互相訴說著彼此的思念和牽掛。
責任:講好故事 無須多言
正觀新聞記者:這次拍攝對您而言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陳舉:這次拍攝對我來說,可以說是一種再教育,心情很復雜。在我看來,這個紀錄片講述的不只是這1300人在兄弟省市學習后回到西藏奉獻的故事,更多的是反映出西藏70年來每一點滴的進步,都和中央、兄弟省市支持分不開。

部分藏族校友合影
正觀新聞記者:您怎么評價這部紀錄片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成績?
陳舉:這部片子基本上該獲得獎項都得了。就作品本身的內容和意義來說,可謂是實至名歸。但于我個人而言,這其實不能算成就,只能算是在講述中國故事、河南故事的歷程中值得紀念的一個作品而已。我們這幾年一直都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對中國、對河南來說,把自己的故事講好,可能更需要的是堅持。做好自己,講好自己的故事,河南需要這樣的作品去為自己證明。
正觀新聞記者 孫珂
